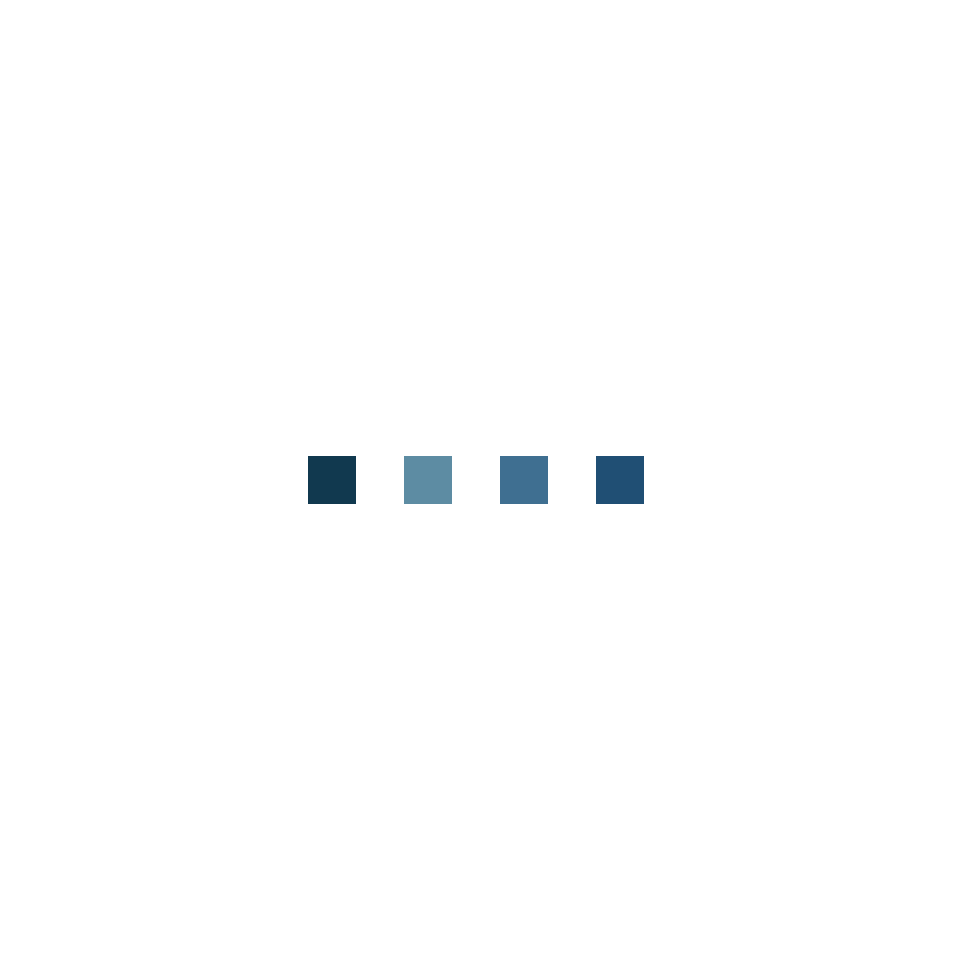第二幕,她換上黑色芭蕾舞衣,搖身一變為妖媚的黑天鵝,身軀更加大膽地旋飛,挑逗著王子,然後進行芭蕾舞蹈中最高難度,並且最考驗芭蕾舞者能耐的「32圈揮鞭轉」(fouett?,單足趾尖旋轉)勾引了觀眾的情緒,跟著她的旋轉節奏拍手,讓整個國家戲劇院彷彿浸在一瓶氣泡水裡。
娜塔莉‧瑪莎克是基輔國家芭蕾舞團首席舞者,日前來台,於國家戲劇院演出全本古典芭蕾舞劇《天鵝湖》《睡美人》。72人的大舞團,後台隨便瞄一位舞者,都是十頭身,直逼法國時尚舞台的超模等級。但這裡沒有香水味,而是瀰漫著肌肉痠痛噴劑、沙隆巴斯的味道。
也許是36歲了,受訪前,舞團經理審視訪綱,要求別詢問與年齡有關的問題,聊未來規劃就好。或者,像童話故事一樣,從好久好久以前說起,背景音樂當然是柴可夫斯基。
小時候,她第一次透過電視看了芭蕾舞劇《天鵝湖》,螢幕裡優雅的芭蕾名伶,讓剛開始學舞的小女孩,腦海冒出許多夢幻泡泡。「家裡沒有大鏡子,但晚上時,如果把窗簾拉起來,就可以在窗戶上看見自己還算清楚的身影。」這時就可以嘗試重現那優雅的姿態。
她以俄語訴說自己成為舞者的過程,那像在敘述一段被決定的人生。「媽媽決定讓我學舞,更準確地說,是我的老師決定的,她建議我媽媽讓我去學芭蕾,因為她發現我有天賦。」4歲進入兒童舞團,10歲進入基輔國家舞蹈學校,穿上芭蕾舞鞋的硬鞋,學習站在腳尖上跳舞。「我一開始並不明白這一切會有多困難。大概是過了5年吧,我才開始明白,大人給了我什麼,以及我一生將從事什麼工作。」
訓練的過程是嚴酷的,那時候的她,沒有感受到快樂,每一日像機器一樣,單調地練習著屈膝、延伸、鞭轉等基礎動作。才11歲,她就受傷了,痛到無法練習,並且因為治療,成了躺在病床上不能動的睡美人。「原因是練習強度很大,而我當時年紀還小,骨架還沒穩定,脊椎有許多處位移。」幸好媽媽帶她四處求診,才治好。
那父親呢?「爸爸很早就過世了。」吻醒睡美人的,不是童話故事裡的王子。她茶色幽深的眸子暗了下來,語氣憂傷不願多說。那神情像是《天鵝湖》第三幕,白天鵝奧蒂特發現王子錯認了對象,與黑天鵝奧蒂莉締結愛的誓約,於是在天鵝湖畔泣訴的樣子。
對父親的記憶只到12歲。她說父親有帥氣臉龐,知識素養也高,雖然不知道父親的工作,但還記得父親回家時,總會帶著礦物的橫切面回來。她也記得父親開車送她去舞蹈學校上課,幫她拉筋。「爸爸在世時,總向別人介紹我是小芭蕾女伶。不過,我覺得他這樣說其實沒有特別用意。在我們國家,小女孩若手長腳長,大概就很容易被這樣戲稱。」說到這邊她笑了一下,「但是沒想到,我最後竟真的成為芭蕾女伶。」
18歲,她終於首次登台,然而演出時,卻成了醜小鴨,「我忘了舞序。我太受震撼了。我練習、彩排了很久,結果一上台,全都忘了。那真的很可怕。」那是2000年,她在前蘇聯人民藝術家塔媞安娜‧塔亞基納(Tatyana Tayakina)的指導下,從基輔國家舞蹈學院畢業,進入烏克蘭大劇院基輔國家芭蕾舞團。從此,生活不是跳舞、排練,就是在表演的旅途上。
她生涯演出超過2千場《天鵝湖》,光是上個月,就演出了20場。我問:「對於童話故事裡,女性總是被男性決定命運有何想法?」但這個問題,經過舞團官方指派的烏克蘭籍男性口譯,變成:「妳應該不像女性主義者那樣,總是覺得自己被壓迫吧?」當下,她回答:「女性的命運受男性制約,這很正常。」
之後我們邀約2次訪談,另一位口譯終於忠實傳達了我們的問題。這一次,她說:「在烏克蘭,民眾對男女平權的問題比較不敏感,但同時每個人都有權利為自己做決定,與性別無關。至於舞劇,男性角色相對於女性,應有更大的主導權、有領袖魅力、有能力保護女性。當然,女性應該有選擇權,男性也應該尊重女性的選擇。但男女終究有別,我想,任何女性最終都會希望自己有夠強大的男性相伴。」或許是父親很早就在她的成長中缺席了的緣故,也或許是演了一輩子的故事,讓她即便卸下舞衣,走下舞台,也仍然活在王子、公主的故事裡。
我忍不住問,那妳現實中的戀愛關係呢?「我的男伴一直都是人格強大的人,我認為這對女性很有助益,也是很重要的支持,男性越強、越值得依靠,女性就會越安心。像我的現任丈夫,他雖然脾氣溫和,但內心世界非常強大,給我很大的安全感,讓我可以很自在地做自己。」她已結婚,沒有孩子,丈夫也是芭蕾舞者。
俄國聖彼得堡音樂學院表演藝術研究所博士李巧說:「只有舞者才會同情舞者的生活,因此芭蕾舞者的伴侶也多為芭蕾舞者。芭蕾舞者的練習強度大,受傷嚴重時甚至無法生育。而不間斷的表演生涯,也讓舞者不會有生育的計畫,等於是將自己完全奉獻給藝術。」
此次來台,劇團人數高達72人。舞者有階級,從排場就能看出來。搭機來台,她與客座首席馬修‧波頓(Matthew Golding)最晚抵達,記者會只由年輕舞者出席,乃至閉幕酒會的進場順序,2人永遠最末登場。
大舞團中人與人的相處是緊繃的,沒有誰會甘願演一個只能襯托主角的角色,也因此有嫉妒與恨。2年前,她的舞裙就遭到破壞,回家後才發現。「那是件3層裙,發現裙子被破壞的是我媽媽,然後我才看到3層裙裡,有一層被剪掉了。」
競爭氣氛也無處不在。此次表演,2組人馬輪流演出,也因此有了對比。《睡美人》第一幕,4位王子輪流向公主求婚,此時飾演公主必須單腳腳尖支撐,讓4位王子依序牽手,緩慢轉圈,時間長達30秒。這一段稱為「玫瑰慢板」,她表演堪稱完美,讓燈控室的工作人員們驚呼議論,只因前一天,另一位首席舞者安娜塔西亞‧謝芙倩柯(Anastasia Shevchenko)中途換腳。
台藝大舞蹈系主任吳素芬教授說:「以古典芭蕾來說,是不能換腳的。也許是舞者受傷,或是其他原因。單腳腳尖支撐,是基本功,但支撐時間久了,就是高難度的動作展現。」
我們向娜塔莉‧瑪莎克聊起這件事,她表情驚訝,雙手不自覺地摸向臉頰,頻頻追問是否屬實?之後優雅的面紗褪下了,小女孩神情也不見了,露出嫵媚燦笑,是成功媚惑王子的黑天鵝奧蒂莉。
「以前,我剛出道(加入劇院演出團隊)時,芭蕾女伶有嚴格的角色區分,一個劇院裡可能只有1、2位女舞者是可以勝任所有角色的。」角色能否演繹,還得看身體素質與氣質,若不適合,「妳永遠都不可能演那個角色。」
「現在,情況變了。舞者獲允許跳任何角色,但技術面就被犧牲了。全能的芭蕾女伶少之又少,因為這不但牽涉到高度的技術要求,還有舞者外型的可塑性。舞者必須有能力塑造出符合角色設定的外在形象,風格上不能有違和。所以 …」她停頓了一下,「我們親眼見證了演出如何被犧牲。」
她歷經多次低潮,也曾想過放棄芭蕾舞,「大概每3年就會有這樣的狀況。」她的臉書封面,放著一張達賴喇嘛的圖片,她說,這與宗教信仰無關,純粹喜歡圖片上的字句。我們請她朗讀,她深吸一口氣,彷彿游入沉靜的湖水,「當人覺得不順遂時,或許正有美好的事物,正試著進入他的生命。」
訪談,讓她像是被架在椅子上的芭比娃娃。她累了,修長的雙腳磨搓了起來,像是渴望自由的翅膀,即便是不耐煩,動作仍然優雅。這份優雅的背後,是嚴酷的打磨,她的腳踝與腳趾,每一處關節都如球狀脹大,彷彿被塞了玻璃彈珠。
想家了。表演是長途的旅行,先到法國又去瑞士,再入台灣,已離家90天。這個深夜,她將從微雨的台北搭上飛機,飛過數十個國度,回到故事的原點,她的出生地烏克蘭首都基輔,那裡有媽媽、哥哥,以及她的丈夫。
還有公園裡水池邊的天鵝。她曾經嘗試揣摩,感受天鵝翅膀的彎折與擺放、脖頸的曲度。「天鵝是驕傲的鳥類,但同時又脆弱、細膩,這應該就是《天鵝湖》中白天鵝的形象吧。」她述說時,彷彿在描述自己。背景音樂依然是柴可夫斯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