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童話.世界》又不是何嘗如此?藉由一場補教名師對女學生們的權勢性交,去走一遍展示性侵性騷在法律上的眉眉角角,「我覺得我有義務要做這件事,要給自己一個交代,如果這個議題能被能理解,它就是一個有意義的東西。」近日,他將這個故事改編成小說,電影未竟之處,話說不清楚的,說得更明白。
【唐福睿番外篇】當性侵性騷舉證困難 《童話.世界》這樣做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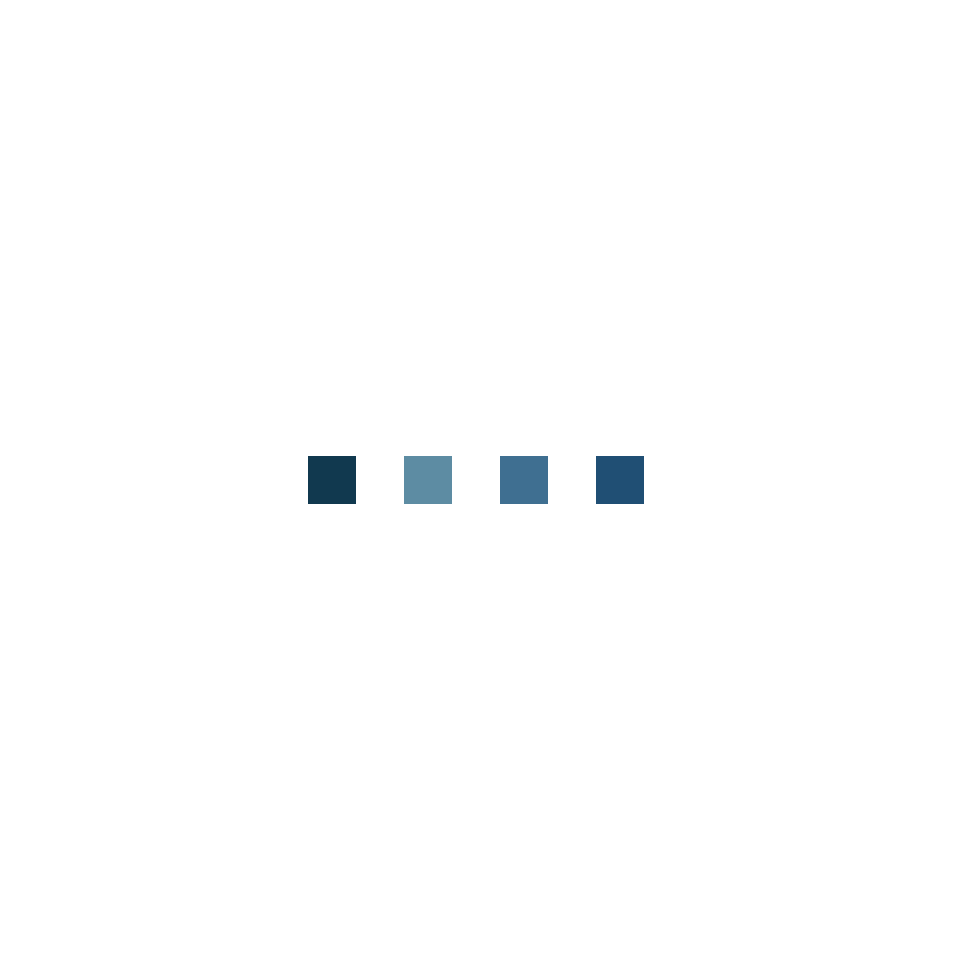
唐福睿《八尺門》寫作策略一開始的設定就是希望把死刑的程序展現在讀者面前,他帶讀者走一遭死刑的程序,聽聽正反兩方的聲音,其餘,自己下決定,「我希望能讓大家輕輕晃動腦袋裡的想法,哪怕只是心底有個很微弱的聲音說『或許我可以重新思考這件事。』」
「其實我最近才把小說寫完,寫小說更需要邏輯說得通,剛寫完,思路特別清楚。法律對性騷擾案件的偵查有其侷限性,但據我所知,狀況也不是沒有改進,就法官也好,警察也好,對於性別、被害者的理解都有在進步,法律也都還在修正,性平三法最近也在修法(7月13日已通過),法規對被害者的保護是越來越周詳,當然操作起來並不是這麼理想,像是現在在推一站式詢問,就是被害者無須去警察局地檢署說明,為了降低被害人痛苦,她報案後去醫院,把相關人士找去醫院,警察檢察官醫生都在,可以當場採證,讓他們可以受到最少的傷害。但這是很理想化的狀況,不是每個縣市都有這個資源去整合這件事。因為他需要很大的成本。我為了寫小說,有重新訪談社工,社工想法跟我差不多,他們都感覺到社會都在不斷的進步,但現實的考慮是很難突破了。
他說的很難突破,是在無罪推論的前提下,性侵本來很難證明,「性侵性騷擾在司法屬於隱蔽型犯罪,證據很難取得,各說各法,我不覺得很難證明這個問題有甚麼辦法解決,因為要訂一個人的罪,它就是需要證據。因為不管法律怎麼修,就是不能變成有罪推定。」
「我不覺得證據這件事法律可以解決。我寫小說的意義就是在這裡,重點是人怎麼看待這件事情,過去被害人在陳述這件事之所以困難,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父權的觀念,我們有一個理想化被害人的形象,這更加深了他們的困難。《童話.世界》就在講這個事情,我的主角是一個男生,他不是一個加害者或者被害者,他代表的是法律的觀點,他前後經歷了幫加害人跟被害人辯護,我們跟著他經歷了法律的程序。電影其實很難理解,小說稍微寫得清楚一點,他最後做的事,爆料甚麼的,他沒有問過被害者,這才是故事的核心,他做的這件事其實是父權的投射,他沒有跳脫這些東西,他認為自己是英雄。性侵的法律在進步,但關於證明與證據,差不多就是這樣。只有我們改變自己的想法,才有稍微變好的可能。」
正值台灣掀起鋪天蓋地metoo運動,受害者只能依據自己的記憶,在網路上爆料、控訴,鄉民們未審先判,然而廖峻的個案是一種標準,黑人陳建州的個案又是另外一種,問他是否擔心法律被傷害了?「我們心裡都還有一把尺,有輕重,有客觀判斷,第一個被害者出來,你否認,第二個被害者出來,你開始躲。那就一定有問題。法律可以處理都太有限了,只能借助這樣做法。」當法律暫時被按下暫停鍵,他說那也沒什麼不好:「我覺得那是一個對抗的過程啦,一定要過頭,大家才能找到癥結點,你假如在運動起來的時候沒有做得很激烈,它不會改變甚麼。」
★《鏡週刊》關心您:若自身或旁人遭受身體虐待、精神虐待、性侵害、性騷擾,請立刻撥打110報案,再尋求113專線,求助專業社工人員。
本新聞文字、照片、影片專供鏡週刊會員閱覽,未經鏡週刊授權,任何媒體、社群網站、論壇等均不得引用、改寫、轉貼,以免訟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