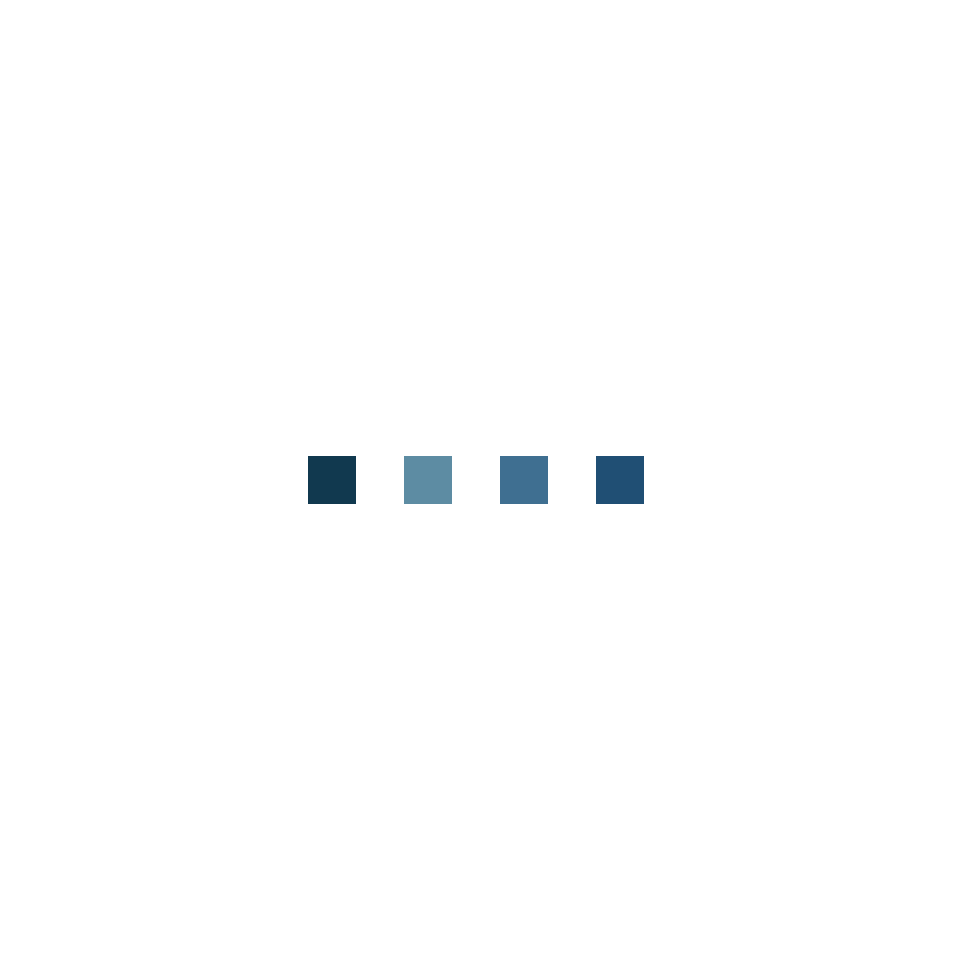年輕人熱衷的儀式感與小確幸,這位80歲老人家早已日日實踐。江賢二每天凌晨4點起床,煮咖啡、放音樂,欣賞太平洋的日出,然後開始工作。
每住一個城市 都是一個故事
於是我們與他約凌晨4點採訪,他的住家兼畫室位在東海岸的金樽,一個介於都蘭與長濱之間的小漁村,我們抵達大門時,一抬頭是滿天星斗,前一天傍晚還有絢麗晚霞,忽然就明白了這位每天要讀《紐約時報》、看CNN,過去60多年都住大都市的畫家,為何從2008年便長居這個偏遠漁村。
採訪在他美麗的迷你游泳池畔進行,前方是太平洋的日出。他遞上兩杯濃濃的espresso,醇厚芳香得堪比義大利咖啡館現煮,他說在台北一間兼售咖啡豆的畫廊買的,接著從屋內拿出手提音響。「咖啡是一定要的,然後一定要聽巴哈,我都放顧爾德演奏的〈郭德堡協奏曲〉,這裡看得到綠島,光線慢慢亮,旁邊有巴哈鋼琴曲,那種境界真的很難形容。」

他住過許多地方:台北、基隆、巴黎、紐約、台東,每住一個城市,都是一個故事。他是知名畫家,幾幅代表作便是在這些城市畫出,他的作品動輒破百萬元,2020年他在北美館辦回顧展,儘管是不太好懂的抽象畫,卻大受歡迎,年輕人搶著排隊拍照打卡。
江賢二早在15歲就決定當藝術家。他出生逢二戰,父親長年在泰國做生意,體弱的母親替人縫補衣服賺家用,但他11歲那年,母親就病逝。他初中讀建中、高中讀師大附中,功課甚佳,然而最後他選擇師大藝術系(今美術系前身)。
畢業後,他短暫在基隆當美術老師,也繼續畫畫,畫室就在海港邊。年輕窮畫家的夢想之地是巴黎,畢卡索、海明威的巴黎。那時機票奇貴,簽證也難拿,江賢二日日望著港邊貨輪,幻想如何偷渡去巴黎。
幸而父親出錢買機票。但終於到了巴黎,他卻短短1年就失望離開,轉往紐約這個活力四射的年輕城市,他驚見那兒的藝術家連帆布都拿來創作,大開眼界,一住30年。
採訪時,我們就在他滿是油彩的小畫室,看到椅子上一疊《紐約時報》。他至今每日必讀,「這裡會晚好幾天送到,有時3、4天擠在一起送,呵呵。」
拒向市場妥協 不願改變畫風
在紐約,他與妻子展開一段料想不到的經歷。他讀師大時認識學聲樂的范香蘭,藝術家多情,范香蘭卻至今是江賢二唯一交往過的女友。「出國前她在國賓飯店唱英文歌,我常笑她的英文歌唱得不好,只是長得漂漂亮亮又會唱英文,人家就給她很高的pay。但她的藝術歌曲唱得很好。」兩人畢業後成婚,浪漫的藝術家笑道:「我到現在還是叫她女朋友。」
江賢二親切好聊,然而,據說從前的他完全不是這樣,在紐約時期尤其憂鬱少話,連朋友都不交。

剛搬到紐約,江賢二到禮品店當售貨員、到餐廳當裝潢工,范香蘭則在廣告公司工作,同樣才華洋溢的她後來開了一間高級訂製服店,「她自己設計,找人家縫製,有時會要我幫忙配色,我就說這灰色應該配一點黃色。」江賢二還兼當送貨員。
他繼續畫, 7年後終於在紐約舉辦個展,只是,沒賣出任何一幅畫。那年代流行普普風,最知名是安迪‧沃荷,江賢二的極簡主義已不時興。他曾遇到知音,那人正是安迪‧沃荷的經紀人,叫艾文‧卡普(Ivan Karp),他開設的畫廊是蘇活區的重心。卡普極欣賞江賢二,但他建議江賢二改變畫風,因為藝術市場不流行極簡風了。
江賢二卻不願妥協。「不能說你年輕時喜歡藝術、決定從事藝術,畢業幾年後卻去畫那些比較商業的東西。你去做什麼工作都可以,去做生意都還對社會比較有貢獻。我的意思是,有一點不值得啦。當然,這很難。」

倒是妻子的服裝店生意越來越好,後來遷到曼哈頓的麥迪遜大道,街上盡是香奈兒等名店,范香蘭的店也不遜色,第一夫人、大使夫人皆是顧客,「每年九月有聯合國大會,大使在開會,太太們就到我們那裡shopping ,有的大使夫人每年都會到我們店裡買衣服。」那時,兩人已40多歲。
范香蘭的時裝店受歡迎的原因之一,是店裡放有江賢二的畫作,整間店味道就是與眾不同。不時有人詢問畫作,例如《巴黎聖母院》,范香蘭總得解釋畫作是非賣品。
那時,江賢二終於畫出滿意的作品。先前他總不滿意,剛到紐約前幾年甚至畫不出來,他說,衝擊太大,需要消化。直到10多年後他重返巴黎,畫出《巴黎聖母院》,才認為自己有資格當畫家。
在很美的地方 難有好藝術品
第一次到巴黎時,究竟發生了什麼?他說,到了巴黎,才知道他最崇拜的雕刻家賈柯梅蒂已在一年前離世。心碎之餘,又碰到著名的1968年5月學運,「我找不到洗碗的工作,那時的餐廳就像現在的Covid-19一樣,都關門了。」
然而,有一個最根本原因,「我對巴黎的當代藝術有一點失望。」太保守?「對,沒有我想像的那麼…巴黎非常漂亮,但我慢慢發覺,比起德國、紐約,為什麼法國的當代藝術沒那麼強,因為這個都市已經太美,很美的地方跑不出好的藝術品,好的藝術品大部分是在痛苦、災難、不順利時,才可以跑出感動人的力量。」

他說,甚至台北都比巴黎有可能創造出好的藝術品,又如2、30年前的德國,「柏林圍牆倒塌,什麼都爆發了。但現在德國又變得舒適了,所以好的藝術又從別的地方出來。藝術都是一樣,不能太安逸。」
然而他到紐約接受當代藝術的洗禮後,卻是回到巴黎才畫出滿意作品,生命奇妙而永難預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