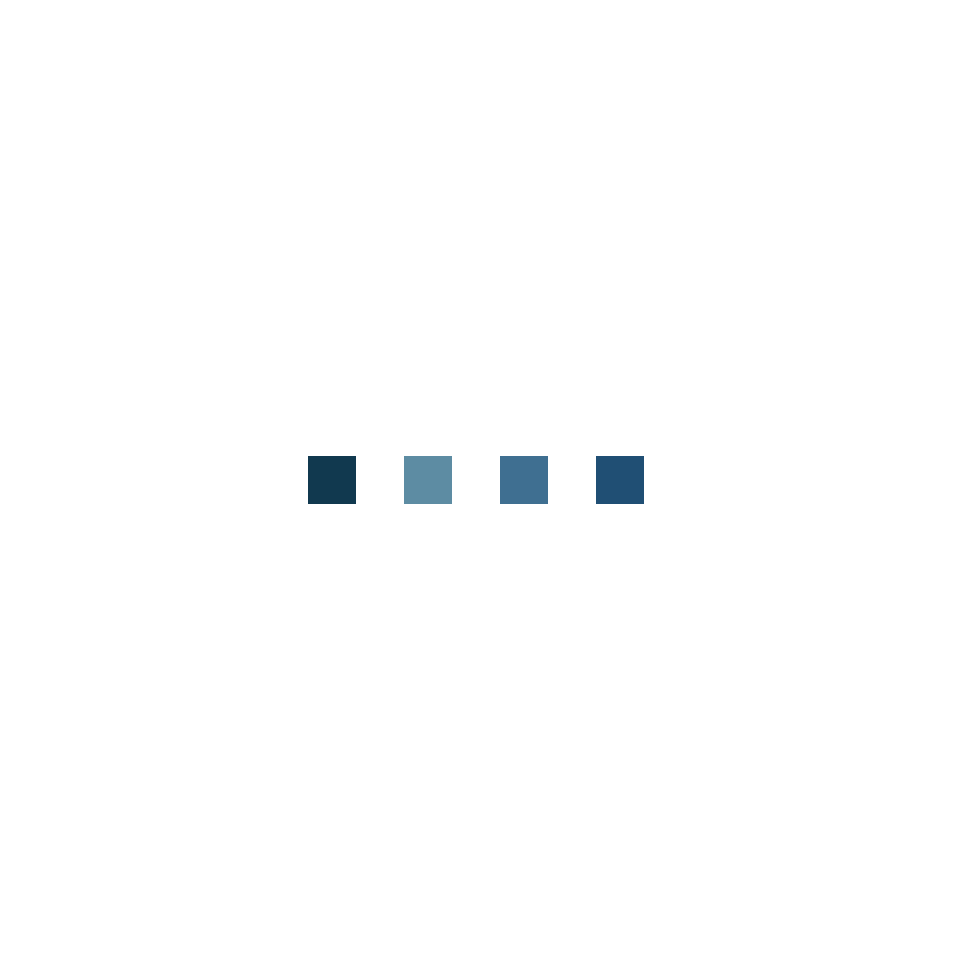有時候看盧郁佳寫書評,比方說因為男人外遇而瘋狂的女人,都印象非常深刻,尤其她最近寫《陽光普照》裡面把家裡打理得非常好,支撐起家裡的那位媽媽,她覺得那是另外一個暴力。她對這些婚姻中的女性,描寫都非常到位。
我一直很好奇,其實郁佳未婚,為什麼能這麼感同身受這些女人的處境,後來想說,那是因為她大量的閱讀小說,閱讀很多的文學作品,讓她得以穿梭在這些不同的生命經歷裡頭。郁佳一年前就知道我在採訪寫作這些女人的故事;半年前,我也陸續把一些書稿與她分享。我從一開始寫女人的出逃,到後來調整成在寫女人在婚姻跟伴侶關係裡的失敗,進而出走跟重生。
這些故事跟小說不同的是,它們全都是台灣女人真實的生命經歷。所以我想問郁佳,她以前看那些小說,她現在怎麼看待這一本類似於報導文學的作品。
盧郁佳:書本的世界,至今都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個男人觀點所主導的世界。格雷安・葛林的婚姻小說描述一個男人的外遇,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經典的形象,至今仍然影響著我們判斷婚姻跟外遇的眼光。
一個老婆病懨懨地糾纏著老公,使喚他去做所有的事情,以自身的虛弱作為要脅來控制他。老公不堪其擾,可是看老婆這麼地可憐,真的是不忍心離開她。然後,外面又有一個女人,更可憐了!也是要向他求助、祈求他的關懷、祈求他的援手,事實上只有這個男人能夠拯救這個可憐的女人。因此,他又秉持著正義的俠心,去跟外面這個女人在一起。
但是,外面這個女人,一旦得到了他的垂青之後,就翻臉搖身一變,就再也不能接受他還仍然留在老婆的身邊,所以也霸道的要求他留下愛情的證物,來證明,哦,這個男人真的是愛她的,如果不是這樣,那麼外面這個女人就會活不下去。這個男人是這麼的善良、這麼的正義跟俠心,所以他還是依照外面女人的要求,給她留下一封情書。
接著,這封情書就會成為敵人打擊這個男人的利器,把他逼到絕境,搞得這個男人最後落得自殺。他簡直就是一個唐吉軻德那樣的俠士,因為他這個人格實在太完善了,所以不得不毀滅,世界不配擁有他這樣美善的人物。
文學的世界經常都是這樣子,完全從男人的角度來看待婚姻、愛情或是外遇,讓讀者覺得說我們要突破傳統的道德倫理規範,應該要同理這個可憐、悲慘的男人,並且尊敬他的正義、俠心還有善良。
但是,如果我們看玉梅的《賢妻良母失敗記》就會知道這一切都是屁。男性觀點的小說,完全沒有理睬他的妻妾在這裡面付出的代價跟傷痛。格雷安・葛林筆下的角色,其實就是跟《房思琪的初戀樂園》裡面的李國華是完全一樣的。李國華誘姦了中學女生,他們長期的關係在東窗事發之後,在老婆面前被包裝成一個外遇。
老婆是怎麼知道的呢?因為房思琪的父母上門興師問罪,他們在飯店房間裡面談判。有罪的是這個李國華,但是師母理直氣壯的撂了一句話,「這裡面,有資格提告的只有我一個人,我要告你女兒誘拐我老公『通姦罪』。」這個大老婆的觀點,不是女人的觀點,是男人的觀點,是護航男人外遇跟強暴的觀點。
可以震驚文壇,可以造成社會現象,是因為她很少見的呈現了女人在我們習以為常縱容外遇、縱容暴力的觀點之下,女性觀點可以呈現出來。而我認為《賢妻良母失敗記》也是這樣子突破性的嘗試。它把真實經歷放在檯面上來的時候,就讓我們看清楚它真正是怎麼一回事,它是一本女人的成長之書,婚姻和童年的傷痛之書。
所以,我不會把它看作是七個失戀或失婚的女人個人私事可以私了,這都是重大的公共議題,讀者不分男女是要帶著血海深仇去追討真相。這七個女人就算是最後接近了痊癒、接近了自由跟自主,她們的損失無法彌補。
陳玉梅:這就是我當初為什麼我要去寫這些女人的故事的原因。很多這個社會會認為,這是些婆婆媽媽的問題,這到底有什麼好寫的?比方說,我在寫這些女人的故事時,我要穿越很多她們在生命經歷裡所遭逢的那些性別歧視、被壓抑的對待、被歧視的對待。我想寫這些是因為這些問題,很多人都把它認為是理所當然。
比方說,這些女生大概都是四十歲,到中年之後才開始她們的青春期,或開始質疑我的成長過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,讓我的婚姻走到今天這一步。又為什麼,她可以忍受她的老公這樣對待她。
這個過程好像是每個女人,都必須要去進行的一種自我反省。
郁佳:我是覺得她們老公應該要被抓去性平。(玉梅笑)我們應該要有一個婚姻性平委員會。這種事老婆一個人做不來,那不是她的錯。
陳玉梅:妳的意思是說,把老公抓去性平是什麼意思?
盧郁佳:就是你現在搞家暴外遇,欺騙你老婆,然後逼你老婆說,「我不要離婚,妳就是要接受我帶女人回來,妳就是要接受我在外面玩女人;要不然我不給妳錢,要不然妳不能生活。」然後這個老婆,因為她不曉得要怎麼找工作、不曉得她可不可以找得到工作,所以她心生害怕,只好不離婚。想要離婚但是又不敢離婚,困在這個婚姻裡面,這件事情就是違反性平啊!
陳玉梅:這個在現實上可以怎麼做?妳看我寫了雲秀,她後來其實是認知到根本不可能去改變男人。這裡面的每一段都是她們認知到,沒有辦法去改變男人。
盧郁佳:性平教育,就是從中小學試著要去改變男人怎麼想。
陳玉梅:等於就是從教育裡,從小的教育就要做這樣的事情。而不是到進入婚姻之後,再做這件事,基本上已經來不及了。
盧郁佳:我說的來不及,是傷害已經發生了,即使這些妳所寫到的這七位偉大的女性,她們得到療癒跟自主,但是她們的傷痛是沒有人能彌補的?我說的就是已經發生、來不及是指這件事。
陳玉梅:那你覺得男人有可能在這裡面改變嗎?
盧郁佳:妳在說有可能改變的時候,好像也是在說,誰應該要負責去改變他們?誰應該去負起改變的責任跟成本?誰要為此付代價?傳統上,我們會認為,女生要去做這件事,因為她受害所以她要去改變他。如果妳老公打妳,妳應該要改變她。但是現實上做不到對不對,所以這個責任並沒有被放在家暴受害者身上。在文明國家,這件事情是社區警察、法庭、親戚朋友、學校教師、警察、法官、檢察官、監獄的獄卒,都負有去改變這個男人的責任,而不是光放在這個女人身上。
陳玉梅:其實聽妳這樣講,我覺得它讓我想到裡面寫的一個雯怡。她說她離婚之後,她先生把她當作是神經病,她先生對於她對他的這些質疑,比方說他大男人、把她當附屬品這一些,很不以為然。然後,他認為所有錢都是他賺的,雖然說他們兩個在婚姻裡面,他們一起創業,可是這男的就認為說錢都是他賺的,然後他老婆做這些事情都不是事情。
所有女人做的這些事情,因為沒有領薪水所以都不是事情。到後來她決定,她不想要繼續再這樣過日子,四十歲她要離開這個婚姻。可是她老公仍然不能理解她到底怎麼了,他又很快找到另外一個年輕的太太,娶了她。
我在這裡只是要問一個問題,到底男人去察覺這件事。比方說我在這裡面,我能處理的是女人的覺察,女人認知到很多事情不是錯在她的身上。回到男人,除了回到教育,我自己覺得看這些女人,好像只能先出走、離開,徹底的斷絕這個關係,讓男人得到一個教訓了,去想好像我以前在婚姻裡面好像出了一些狀況了。
要男人改變,似乎是非常非常困難的。我在這本書,我說實話是沒有看到的。那個男人好像是永遠僵固不動,可能因為是男人永遠的社會位置其實有很多的紅利,他怎麼樣都有辦法找到新的對象,比女人容易得多,所以他不需要去改變。
陳玉梅:其實這七個女人歷經婚姻暴力的,很多都沒有被處理,它就是黑數。比方說像余莉的媽媽,那個婚姻性暴力,她甚至認為說這個是理所當然的,好像進入婚姻,她就必須要接受這些。或者雲秀,她老公外遇,她要求她老公不要出去,然後她被揍,她還要認為說,啊就是因為她阻止了他;或者她老公會說「誰叫妳要阻止我,妳就放我出去就好了啊!」
所以我後來回頭看我這本書,這本書的價值可能就是在於今天這些女人她實際的說出「這些男人根本不認為是問題的問題」,因為他們的立足點根本不同。所以我剛才會講說,男人要改變,就我看到在這麼多黑數的狀況底下,男人的改變到底如何可能?
盧郁佳:男人的改變不但可能,而且在改變,我們今天做的每一件事都在改變男人。書中,有位太太要離婚,她老公是不答應的,但是猜怎麼著,她說:「我手上有驗傷單。」幸好這位太太的姐妹告訴過她,每一次被打都要去驗傷,所以她留下了她的籌碼。她要離婚的時候是可以離的,因為她手上有驗傷單。
為什麼,女人可以有驗傷單?為什麼法官必須要把驗傷單當一回事?因為前幾百年的女性,拋頭顱、灑熱血去爭取改革,這件事改變了男人。這個男法官必須要把驗傷單當一回事,這檢察官必須要把驗傷單當一回事,醫院必須要把驗傷單當一回事。女人被打,必須要被當一回事。
這件事已經改變了。所以我們要相信改變,我們要投身改變。
陳玉梅:OK!妳喚醒我的記憶了。
盧郁佳:對,我們不要絕望,我們在改變之中。
陳玉梅:我剛在想說我寫這七個女人,我覺得都好悲慘哦!就是有些甚至都沒有辦法,在社會的要求底下,又不敢離婚,像雲秀她其實也很討厭做愛,可是這些都被迫。她們後來的確是靠著《家暴防制法》,她們才能夠離開那個可怕的婚姻。
其實沿著郁佳的脈絡,回到那個怡雯,她先生的確也有些改變。就是她先生後來再娶了太太,他就不敢這樣子對待他的新婚妻子。他不敢再要求說,妳要無償地幫我做家事,所以在書裡面,怡雯就非常不平的是,她以前做家事都是無價的,甚至被認為說這些都不是事。可是她前夫的新婚妻子是,所有的家事都是他前夫做,他甚至讓他的新婚妻子安心的在外面工作。
所以也許是前一段的婚姻的這些過程,讓這個男人學乖了。
盧郁佳:所以她覺得很不開心,妳覺得她是因為不開心這個新太太不應該得到更好的待遇呢?還是她不開心這個先生雙重標準呢?
陳玉梅:我想都有吧。可是更多的是那種,覺得說為什麼我就不值得這些呢?那個太太怡雯可能會覺得,為什麼在婚姻當中我就不值得這些呢?說實話,我覺得這個問題是讓人覺得滿悲傷的。我覺得這些女人都會問,為什麼我就不值得呢?
盧郁佳:前年同志大遊行的時候,我站在台大醫院旁邊舉牌,就有一些同志朋友站在那裡跟我聊天。大概四、五十歲的同志,他們會告訴我,今天年輕同志可以站出來、走在街上、告訴別人自己是同志,這件事情在他們年輕時候是根本沒有辦法想像的。
他們可能是跟祁家威同輩,他們說道,祁家威其實是他熟人的熟人,其實離他非常近的。但是他們沒有辦法想像祁家威可以達成這樣的改變。他說,自己年輕的時候,這些事情是根本不敢想,也沒有期待,所以到今天說要爭取同婚平權,對他們來說,有沒有爭取到,都不是很重要,因為本來就沒有想要,甚至會感到不平。
他們覺得,天哪,這群人好像臉上青春無憂,從來沒有受過壓迫,就會覺得自己實在生得太早了,對自己覺得很委屈、很不平。甚至不會站出來的,可能是一些在櫃內陷得更深的人,他們會覺得,如果真的有這些人,根據韓國瑜太太李佳芬的說法,這些同志是不喜歡有同婚專法這些東西。她就覺得同志不要出來擾亂社會,我們靜靜的就好了,互不相擾。
陳玉梅:對啊,這七個女人有一個小蘇就是這樣,她現在每次來信義計畫區裡面,甚至之前台北市政府還掛上了那個彩虹旗。她看到周邊的男男女女,都可以互相擁抱、牽手,她非常的羨慕,可是回到她自己的生命經驗,她卻覺得她根本不贊同同婚。她覺得只要給她一個小小的空間就好了,她覺得她不要違背這些社會的倫常。然後她對於無法自己為養父母傳宗接代,她感到非常的愧疚。(郁佳:對。)
其實是非常悲傷的。或是說她覺得這些女人通通離她而去,她沒有想過說,這些女人離她而去就是因為她們沒有辦法忍受這種,妳因為沒有辦法得到這個社會的認可。可是她覺得她寧願嫁給渣男,渣男至少給她這種合法婚姻的框架,讓她可以跟別人講說,我有婚姻,可是小蘇就沒有想到這一點。
說實話,當她說她非常羨慕現在年輕世代的時候,我真的感到非常非常悲傷,好像就是,他們認為,我就是生錯時代。
盧郁佳:那麼要如何面對這種悲傷呢?我認為,小蘇告訴妳的故事,只是訴說的開始。當她在這個社會的氣氛之下,可以允許她更深地去注視傷痛,當這個傷痛可以被說出來、可以找出來,她想要的是什麼,可以去面對的時候;當她允許自己去擁有那樣的自由,她才會允許別人去擁有那樣的自由。
這是訴說的開始而已,它不是終點。也就是說,當她會有那樣委屈的心情,覺得「為什麼是她,不是我?」那表示這個訴說還沒有結束。
陳玉梅:其實回應郁佳,延伸她現在談的這個東西。我自己也覺得,我這個七個女人的文本是開放的,就是他們每一個都有變化的可能。就像我回頭在看,比方說我寫的某一個女人,她有一些部分我自己一直沒有辦法理解,我一直到今天我才理解,為什麼她會那樣子。
然後那個東西我就沒有辦法,在當初在寫這些的時候解釋。可是因為一直延伸,時間的關係,或是我知道更多她的事情,然後我對那個東西有個重新的理解。
所以我覺得這七個女人代表其實重點不是她們是誰,重點是說,她們就是代表我們身邊的姊妹們。這七個姐妹們,提出了一些我們共有的問題,這些問題呢,我覺得需要我們在這個問題之上,去發展我們自己的答案;或者這些女人也在繼續發展她們的答案。
像我剛剛想到是說,小蘇會不會在同婚法通過之後,她會不會兩年之後來告訴我,她已經結婚了。然後她真的覺得同婚這件事情非常得好。其實我覺得這是可能的,因為妳想想看,她今年才64歲,如果按照我們平均的餘命是大概80歲,她其實還是可以在她的晚年,在她還有十幾、二十年的生命裡面,她可以真正的享受她想要的這種伴侶關係、或者是婚姻關係。這樣來看我這本書真的還滿有價值的。
陳玉梅:郁佳還有什麼要說的嗎?
盧郁佳:就是,沙漠裡面可能可以連續乾旱好幾年,看起來那裡是一片荒蕪的、死的,只有水牛發白的頭骨,跟風滾草滾來滾去。看起來,是沒有任何生命跡象的。可是,雨季來了,突然下了一陣大雨,甚至是下了好幾天,那麼一過,沙漠會一夕之間變成一個怒放的花園。
因為沙漠裡面的植物,有很多捱過乾旱的方式。它會休眠,藏在地表之下,完全看不出來有任何的生命跡象。但是只要環境一改變,把訊息傳給它,變化就在看不見的地方開始醞釀。也許不會像沙漠的花季,馬上瞬間就生長、交配,然後再挨過下一次的乾旱。可是,人心跟那個是非常像的。
像小蘇,或是其他的女人,處在一個極限惡劣環境裡面,其實她有一部份是休眠狀態的,她是不能夠讓任何人接近的。雖然乍看之下,她適應得非常良好,她非常的世故、手腕非常靈巧,她沒有什麼道德包袱,所以她可以把自己照顧的非常好。可是,於此同時,她做出了非常大的犧牲跟退讓,把某些部分放到了休眠區。
而傳統的改變方式,是先從傾聽跟訴說開始。先有你的傾聽,才會有訴說。
玉梅:所以我覺得應該有更多這樣子的書寫,甚至女人自己要出來寫。因為這些經驗,妳沒有寫出來,她就不成為問題。像我剛剛其實就在想說,回頭去看,我剛開始覺得說「啊!這些男人不可能改變。」我就在想說我當初為什麼沿著剛剛談話的脈絡,會這樣講是因為,我在寫這七個女人的時候,有時候會覺得,黎明天光到底什麼時候會出來?
其實,這七個女人幸運的是說,終究還是看到了一點點希望。可是有多少女人,其實是還在那個暗夜裡面,就她們還是困在裡面。這個東西如果不寫,就是被認為理所當然的。
盧郁佳:妳就是天光,妳寫這本書,所以妳就是天光。
陳玉梅:其實我是不敢說我自己是天光。我覺得,我應該真的是看到了身邊很多女性困在這裡面,好像不寫,她們就消失了;不寫,就一代又一代複製著這個悲苦的命運。
像很多女人會覺得說,她就是命不好。她會把她沒有辦法理解,或者是,她其實只是不知道她還有別的選擇。今天如果她看到前面一堵牆,她只要稍微往旁邊看一下,其實旁邊就是一條路。我今天寫這些,或者也是我對我身邊女人的一種敬意。其實也就是在她們的故事之上,開出了一些花朵。
我覺得我這本書也是,所以這是一個起點,然後我真的希望多一點女人出來寫,寫這些故事,這裡面有非常非常豐富的東西,這是我們女人是我們用生命換來的,如果不留下一些什麼,真是太可惜了,太可憐了。這個命運就是不同,我想這故事的結局就不一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