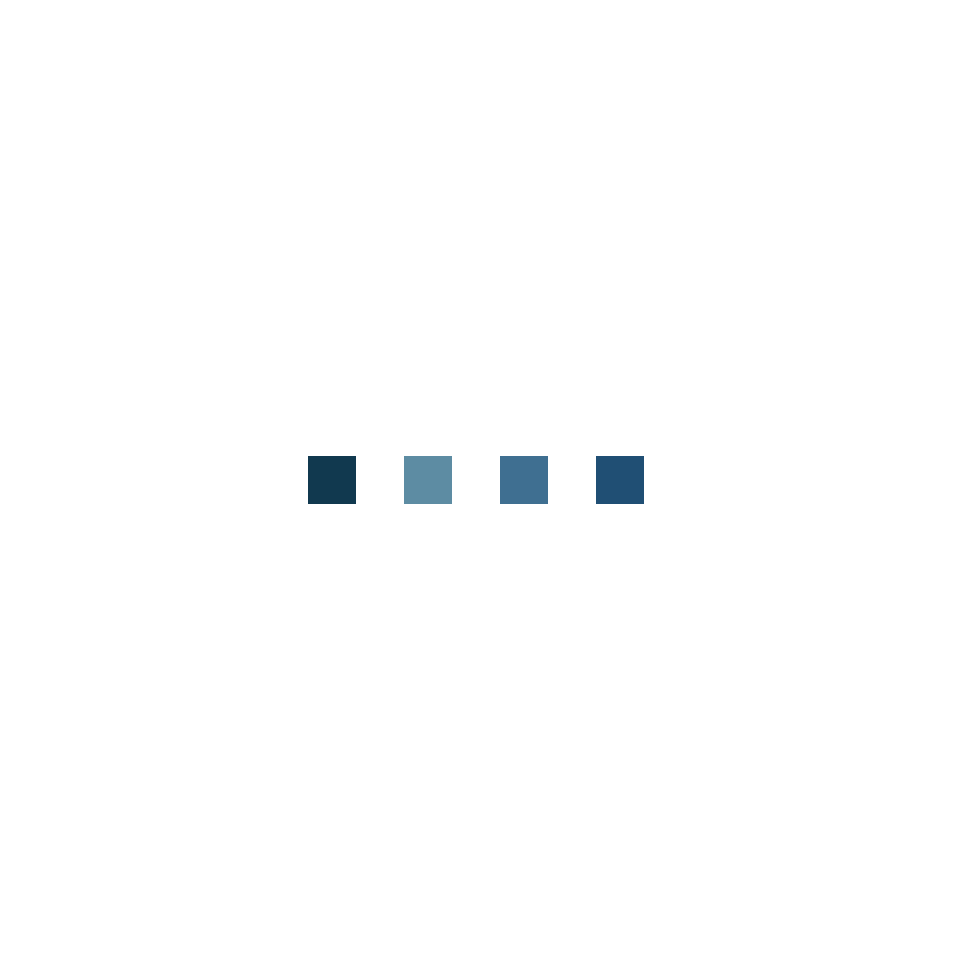中國人的未來也會關乎到台灣未來的命運。
趙思樂(以下稱「趙」):我的主要任務是打書,跟台灣讀者介紹我的書,也跟大家溝通中國目前運動、政治的現況,包括年輕人的情況、社會中普通人的情況,所以我遇到不少來參加活動的台灣朋友們都滿熱情地問我問題,大家的社會雖然不太一樣,但台灣的朋友對中國還是滿好奇的,不管感情色彩或立場怎麼樣,大家都想知道中國的真實情況。滿多人都覺得中國人的未來也會關乎到台灣未來的命運。
《她們的征途》這本書的主要濃縮期是在2003-2017年間,五組女主角分別代表中國民間運動主要的五條路徑,包括異議知識份子的路徑、法治維權的路徑、NGO公民社會的路徑、互聯網運動的路徑,以及草根行動者的命運,代表人物分別是知識份子艾曉明教授;法治先鋒用2015年7月份發生的大抓捕事件,被捕律師妻子們眼光所看到的法治維權路徑;NGO的路線是寇延丁,她是在太陽花運動跟雨傘運動之後,因為這兩個運動在中國國內產生的蝴蝶效應而短暫被捕,所以某程度上她的命運也反映著公民社會裡,中港台之間某種隱喻的連結;互聯網的路徑是一名叫做王荔蕻的大姐,她其實是在50多、60歲的時候才觸碰到互聯網,因而投入轟轟烈烈的運動當中,也成功組織了1989年後最具組織性的中國街頭運動;再來是性工作者出生的葉海燕小姐,她為了性工作者的權利,作為一個草根出生的女性,走過了所有菁英們創造的中國民間運動的路徑,包括她成長為野生的知識份子,成為NGO界的大佬,最厲害的就是成為網紅,從一個底層出生的女性,後來變成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女性意見領袖之一,是非常了不起的。
在自由世界生活的人,可能很難想像在中國的環境下,要去做採訪、發表自己的報導,哪怕只是想讀一本書,或能夠聽到一些信息,都是非常艱難的事。
鏡:那我們來談談你當記者的機緣吧,許多採訪你的標題,都寫說你是「被台灣和香港教壞」,因為你出生在廣州,在那裏可以看到24小時港台的節目,看得到台灣名嘴,也對政治或新聞自由的想像是有一定超然的。但是長大後真的開始以記者身分自居,是什麼時候呢?
趙:大概是從我2011年到台灣作交換學生開始,當時我在高雄一所大學交換,那年剛好是馬英九對戰蔡英文的總統大選,這是個讓我可以真正看到電視裡的台灣選舉是怎麼樣的、非常好的機會。我在高雄跟台北之間不斷穿梭、去了非常多選舉場,我還記得當時蔡英文的競選路線,是台一線從南到北,第一站在墾丁,那次我也搭了好幾個小時客運到鵝鑾鼻聽蔡英文的政見發表。那時候的經歷對我影響滿多的:脫離原有的社會環境,到一個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社會,用這種方式學習做新聞,所以我寫了滿多政治觀察和報導,在台灣的《新新聞》和香港《陽光時務週刊》刊出。做為一個中國的交換學生,就可以在台灣時把自己的報導寫到正式媒體上,其實給我一種非常大的鼓勵,讓我覺得說如果想做一件事情,去努力、嘗試,抓住各種各樣的機會,其實是可以成的。所以我回到中國後,也想像這樣去做些運動的新聞,才發覺原來會有很多阻礙、原來會遇到很複雜的情況,但其實那個初始的信心,和之前有成功作出想要的東西,這種感受會一直鼓勵著我:可不可以再努力一下、再堅持一下?
這幾個月我試著把一些《她們的征途》的書訊分享給中國那邊的人,但是微信和微博上都沒辦法寫這個書的名字,我有時就直接不寫書名,將書封照片顛倒過來,但還是很快會被刪掉。有些淘寶的店鋪會願意幫讀者代購這本書到中國,但據我所知這家淘寶店已經至少被刪了三次購物的連結。可是我還是能感受到國內讀者的熱情,他們會想各種各樣的辦法,專程飛到香港去找很多家書店,所以這本書在香港也是一次次的斷貨,現在可能已經斷貨到第三或第四次。在自由世界生活的人,可能很難想像在中國的環境下,要去做採訪、發表自己的報導,哪怕只是想要去讀一本書,或是能夠聽到、看到一些信息,都是非常艱難的事。
後八九一代的人,由於他們的成長過程中,中國已經是一個相對穩定強大、不斷崛起的國家,他們不太意識到要去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。
趙:「後八九一代」指的是在天安門事件之後才成長起來的青年人。中國的信息封鎖非常嚴重,所以出生在80或90年代之後的年輕人,幾乎很少有機會可以知道89事件。也沒經歷過連中國共產黨都非常徬徨的80年代,當時並不知道是要走市場經濟的開放路線,還是繼續維持計畫經濟和封閉的國家?經歷過那個年代的抗爭者,我覺得他們其實有一種信心是:只要我們夠努力,或只要付出很大的犧牲,我們是可以轉變這個國家的未來和政治體制的。但後八九一代的人,由於在他們成長過程中,中國已經是個相對穩定和強大、不斷崛起的國家,他們不太意識到要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,更加考慮的其實是社會的問題:像是性別問題、反歧視問題,疾病戶籍等民生問題,所以低政治性是其中一個特徵,另一個特徵就是低對抗性。我們前一輩的運動者因為見證過天安門廣場的坦克開過長安街,真的是鮮血灑在長安街上,所以他們的對抗性是很強的,像我知道的一些前輩運動者,他們是坐牢就坐牢,哪怕是被判20年,坐了10幾年出來,又繼續回去做運動,又被判將近10年,他們準備好要付出非常大的代價,像劉曉波先生就死在獄中。但後八九一代的青年運動者,由於一開始只想改變一些具體的問題,很少想著自己要為這件事情坐好多年牢,或是一生的幸福和一生的安定都投入運動中,所以他們很多人是從NGO出生。
但是呢,後八九一代的低政治性和低對抗性情況,某程度上在這一兩年的高壓中發生一種轉變。因為他們本來只想做做性別運動、LGBT的運動卻遭到打壓,他們當中一部分人可能會做更溫和的事,或乾脆退出運動的場域;但是留下來的人會更了解政治現實,準備好願意去坐牢。但現在的情況非常艱難是說,大家幾乎就是動不了,中共的政策這幾年也比較明朗,他就是要全面壓制社會運動的可能性,現在中國民間運動的空間可能已經...算是退回了90年代的情況,倒退了差不多10年的路程,所以其實是滿悲觀的。
曾經的運動、曾經活躍的人,現在不被寫出來的話,他們就有可能永遠被遺忘。
鏡:這本書裡的五位女主角,原本只是芸芸眾生中平凡的人,甚至有點保守,卻都因際遇而成為抗爭第一線的女性。而2014年你面對前夫柳建樹被當局抓走,成為抗爭者時,是否也經歷了相同路徑?
趙:我覺得大家的命運都是被時代和際遇推著走的,很多人並不是一開始就想去觸碰政治,或想要在前線抗爭,卻發現這個政治現實,會把我們一步步拖到那個地方。而我跟這五位女主角的相識過程,也並不是採訪時才認識她們,而是在更早之前就與她們有命運的交錯。像艾曉明教授,她是中國第一本比較系統性女性主義理論的教材翻譯者、編者,我當時在台灣交換,完成大學學業後,先放下了記者的工作到一個女權NGO工作,艾曉明的著作就成了我的入門書籍,以及在女權NGO期間會覺得艾曉明持續的發聲和行動,會一直給我們鼓舞和啟發。或者我的前夫(柳建樹)其實是跟NGO路線的代表寇延丁女士,因為太陽花和佔中運動同一波被逮捕的。他被抓某種程度上是毀滅了我當時的人生,還在女權NGO工作的我,
跟大多數我說的後八九一代NGO工作者一樣,並不想去涉及最敏感的政治問題,甚至我還去逃避,面對一些太可怕的事情也不想去聽、去看,自己最明確的人生目標大概也只是希望有一天能擁有自己的女權NGO,一輩子在性別領域裡工作,但卻遇上前夫被抓,讓我不得不停下手邊的工作,還要面對我自己被敏感化,家庭也破碎。前夫之所以會變成前夫,很關鍵的就是他被抓之後,激化了我跟他的家庭,包括跟他的矛盾。因為他的父母是公務員,不能接受我高調的動用國際媒體或外交官,去救援我的丈夫。他出來以後反而我跟他家庭的矛盾,已經很難再去修補,或許也是我們做不同人生選擇的時刻。
即使知道寫出這本書會面對一些代價,我仍覺得這件事是值得我去做的,因為面臨打壓這麼嚴重的情況下,這些曾經的運動、曾經活躍的人,現在不被寫出來的話,他們就有可能永遠被遺忘,至少是被主流的世界遺忘,你多年以後要再尋訪這個紀錄,反而會變得更加不易,因為這個打壓和信息封鎖都會持續很久。所以我覺得選擇在這個運動被打壓地最深、或是剛剛被打壓到一個低點的時候,去總結過去十幾年的運動,把他留在自由世界的出版物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