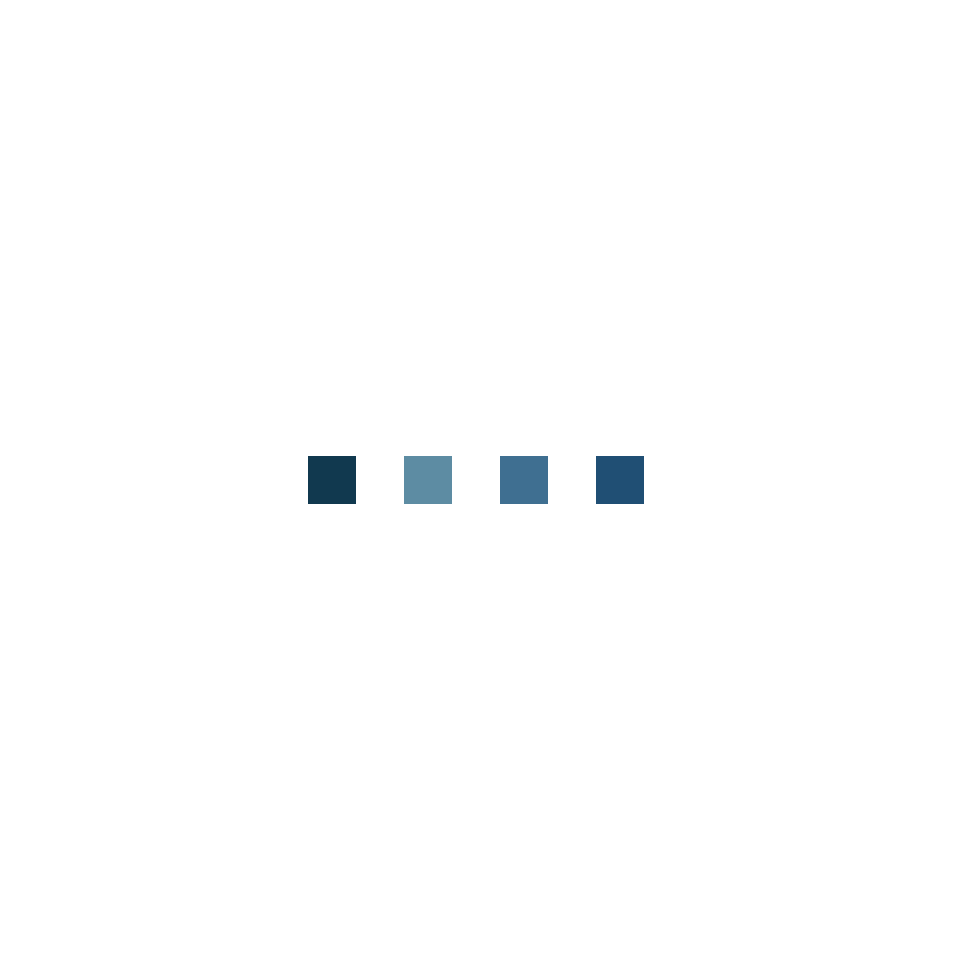此刻我正準備與相伴多天的翻譯Berke Şahan告別,送他去7公里外的野地醫院,當外籍醫療團隊的口譯志工。地震後,哈泰省的醫院全數無法運作,當地也沒有足夠的醫師,所有病患、受傷的災民都必須前往此地就醫。

2月10日,我一抵達阿達納就發現大事不妙。在這個機場尚能運作,提供災民安置轉運的大城,所有資源都已優先提供給各國搜救隊及災民,根本找不到翻譯地陪(及住宿)。透過好幾手轉介,我才終於聯繫上今年20歲、正在就讀阿達納科學科技大學英語系的Berke;他剛好結束在西南部的安塔利亞(Antalya)的單車手訓練返回阿達納。
Berke的同學及朋友們多數都正在當口譯志工。地震發生後,共有88組國際搜救團隊前來災區救災,需要大量口譯人員。他的同學有人隨搜救隊出任務,有人則在機場協助引導。他們組成Whatsapp群組交換資訊,以自身專業幫助國家及災民度過難關。

於是當Berke在阿達納陰暗老舊、充滿香煙味的飯店大廳見到我時,他面露失望,「我以為是要幫助搜救隊,所以志願來做翻譯,當我看到你,才發現原來是媒體⋯但我很喜歡你們,你們需要幫助,讓世界知道這裡發生了什麼事。」Berke依約陪我至災區採訪,但事後對我坦承此事。
這幾天,Berke與我建立起信任關係。他工作認真,面對軍方能冷靜說明來意,說服對方受訪;也會仔細記下受訪者的聯繫方式,「或許你之後可以把報導寄給他們。」有時他覺得自己翻得不好,還會事後索取錄音檔重聽。
當我在完成第一篇稿時,他得知重災區哈泰省有60名美國醫師進駐,迫切需要口譯,因此決定結束協助我的工作。這天,他陪同我完成安塔基亞市採訪後,便將留在當地2、3週,協助傷患與外籍醫師溝通。
這更符合他原先的心願,卻一度在出發前打消念頭。「我猶豫了…」他苦澀笑笑,「我想到你可能在那裡發生事(指遭到逮補),弄丟身分證、無法借到睡袋,身上沒有衣服,而且地震發生後我還沒見過家人。如果只是尋常日子,一週沒見到他們其實不是問題,但經過地震,我真的很想見到他們。」

Berke的家人都住在科贊(Kozan),是阿達納省步調緩慢的古老小鎮,他們在地震中安好,只是房子有些龜裂;但他大學最敬重的老師在地震中罹難,抵達阿達納隔天,他還參與了朋友母親的喪禮。經歷災難,他一樣恐懼和不安。
驅車往安塔基亞市的路途上,Berke接受我的採訪。途中我們經過他原本假日預計要跟朋友出遊的海港城市,「我們本來想在這個海堤上吃點烤肉料理,不過地震發生了,現在我要去哈泰當志工。」窗外風光明媚,草原遼闊,高山還覆蓋著積雪;但隨著越來越靠近哈泰省,手機收訊開始斷斷續續,眼前出現越來越多倒塌的房屋,尚能運作的ATM前總是大排長龍。氛圍越來越緊張。

「其實最近我都不想看任何跟地震相關的新聞,但我現在就身處其中,在我們的書籍、可蘭經中都教誨要互相幫助,其實只要是是人類,就會幫助別人,幫助別人時,不會讓你失去什麼,」 他也提起我們一起採訪時的經歷,「從災民訪談中我發現他們很需要幫助,我可能跟他們深陷一樣的處境,我確定他們會幫助我,所以(即使曾猶豫)我還是決定去(當志工)。」
他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,總盡可能完成1天5次的禱告。路程中他也在迷你巴士中鋪上軟墊,向南方祈禱,「這讓我冷靜,雖然在冬天要洗臉、洗腳、洗手很冷,但信仰讓我有力量做這件事,我們的力量來自阿拉。」

前晚我借宿他在科贊的家,受他家人熱情接待,奶奶端出自製的糕點、手桿的土耳其烤餅;他家牆上的伊斯蘭日曆上,2月13日這天的箴言剛好是:「敞開你的雙手、餐桌及你家的大門!緊閉你的眼睛、舌頭以及腹部(指口腹之慾)。」
我問Berke的父親擔不擔心送孩子去哈泰省的重災區?他回:「一點點,我們並不清楚那裡的情況。」他與家人忙進忙出替兒子整理行李,打包毛毯、禦寒衣物,並在盯著地震新聞時,露出擔憂的表情。

Berke的父母幾乎一輩子從未離開家鄉,作風保守,但仍鼓勵孩子踏上旅途,無所畏懼地幫助別人。那夜他母親將他抱在懷中入睡。「我媽問我可不可躺在我身邊?她抱著我,摸著我的頭髮開始禱告。那是一件很親密的事情,我靠在她的胸膛上,她在我耳邊不斷呢喃低語,窸窸窣窣禱告的聲音,就像ASMR(大腦抒壓),很舒服,」Berke在車上堅定地說,「一切都好多了,我已經準備好要去了。」
在安塔基亞市完成採訪後,天已經全黑了。親眼見識這座城的傾頹與恐怖,他眼底流露疲憊,在車上我們停止聊天;直到因為小巷中間立著一個冰箱,動彈不得,得倒車繞路時,我們才覺得太荒謬而笑了出來。

當晚,我們繞了40分鐘才終於抵達僅僅7公里遠的野地醫院。Berke將行李與睡袋搬下車,身影漸漸隱沒在受軍方管制的大門口。他將在第一天負責醫院櫃檯的翻譯工作,之後將會在診療中協助外籍醫師看診,「有很多醫療名詞,對我來說應該會是挑戰。但我很想學習,這會是一個很好的經驗。」
此時他已準備開始另一趟旅程,懷抱著信念與力量,相信他與他的同胞們會度過這場災難。